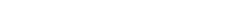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诈骗罪、非法经营罪的关系
作者:陈兴良,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标题:《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性质与界限》
载于《政法论坛》2016年第2期
摘 要:根据是否存在实际经营内容,传销可以分为经营型传销和诈骗型传销。在刑法修正案(七)设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之前,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经营型传销行为按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传销是指诈骗型传销,因此该罪与诈骗罪之间存在特别法与普通法的法条竞合关系。随着司法解释将团队计酬的经营型传销行为非犯罪化,传销犯罪的范围被进一步限缩。
关键词:传销;经营型传销;诈骗型传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刑法修正案( 七) 》增设的罪名,该罪的设立为惩治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与之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正确地把握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性质,合理地划清该罪与其他犯罪之间的界限,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立足于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性质与界限进行法教义学的分析。
一、居无定所:传销犯罪的前史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虽然是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的罪名,但并不意味着在刑法修正案(七)设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之前,该种行为不受处罚。事实上,此前,我国行政法规就明文禁止传销活动,传销行为经由司法解释得以暂时栖身于非法经营罪之中。但因为缺乏传销犯罪的独立罪名,使其处于一种居无定所的状态。可以说,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设立存在一个演变过程。正确地对这一立法过程进行梳理,对于我们把握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性质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对于传销活动的禁止,始于 1998 年 4 月 18 日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鉴于传销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负面作用,国务院发出通知明令禁止传销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通知》第 2 条指出:“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禁止任何形式的传销经营活动。此前已经批准登记从事传销经营的企业,应一律立即停止传销经营活动,认真做好传销人员的善后处理工作,自行清理债权债务,转变为其他经营方式,至迟应于 1998 年 10 月 31 日前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逾期不办理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其营业执照。对未经批准登记擅自从事传销经营活动的,要立即取缔,并依法严肃查处。”这一规定向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在《通知》发布之前,传销是被法律所允许的,并且从事传销经营的企业还经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登记。那么,这里的传销与此后被禁止的传销是否属于同一个概念呢? 这是令人疑惑的。上述《通知》并没有对传销这个概念进行定义,因此也就无从了解法律所允许的传销的含义。在此,似乎混淆了这两个概念,这就是传销与直销。
传销与直销是两种不同的商品销售模式,在现实生活中两者往往被混同。2005 年 8 月 23 日国务院颁布了《禁止传销条例》,同日,国务院还颁布了《直销管理条例》:两个条例分别代表了对传销的禁止和对直销的允许的截然相反的法律立场。
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 2 条的规定,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上述《条例》第 7条还采取列举方式规定,下列行为,属于传销行为:(一)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二)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三)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在以上三种传销行为中,第一种行为属于拉人头,第二种行为属于收取入门费,第三种行为属于团队计酬。在以上三种行为中,收取入门费的传销较为容易认定。而拉人头和团队计酬的传销则不太容易区分,两者的区别在于:拉人头是单纯地以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而团队计酬则是以发展人员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传销活动的特点在于发展人员,在组织者或者经营者与被发展的人员之间形成上线和下线的关系,上线从下线获取一定的报酬。
根据直销管理条例,直销是指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以下简称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因此,直销的特点在于:直销员向消费者直接销售商品。
这种销售方式免除了中间环节,是一种无店铺的销售,因此具有经济性。从层级上来说,直销可以分为单层次直销和多层次直销。换言之,无论是单层次直销和多层次直销都属于直销的范畴。但根据我国直销管理条例,单层次直销是经批准允许存在的直销经营模式,而多层次直销属于传销,是禁止传销条例明令禁止的经营行为。应该说,法律允许的直销和法律禁止的传销之间还是存在明显的区分:从计酬方式上看:直销人员之间没有连带关系,依赖个人业绩计酬。而传销人员之间具有连带关系,实行团队计酬。此外,传销活动的组织者或者经营者要求参加者通过缴纳入门费或以认购商品等变相缴纳入门费的方式,取得加入、介绍或发展他人的资格,并从中获得回报。而直销公司则不收入门费,只要符合一定条件,即可依法取得直销员的资格。
虽然禁止传销条例是 2005 年颁布的,但如前所述,对传销活动的治理始于 1998 年,当年 4 月 18 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此后,2000 年 8 月 13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工商局、公安部、人民银行《关于严厉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等非法经营活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一》),《意见(一)》第 2 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下列传销或变相传销行为,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予以取缔;对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公安机关,按照司法程序对组织者依照《刑法》第 225 条的有关规定处理: (一)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组织网络从事无店铺经营活动,参加者之间上线从下线的营销业绩中提取报酬的;(二)参加者通过交纳入门费或以认购商品(含服务,下同)等变相交纳入门费的方式,取得加入、介绍或发展他人加入的资格,并以此获取回报的;(三)先参加者从发展的下线成员所交纳费用中获取收益,且收益数额由其加入的先后顺序决定的;(四)组织者的收益主要来自参加者交纳的入门费或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的费用的;(五)组织者利用后参加者所交付的部分费用支付先参加者的报酬维持运作的;(六)其他通过发展人员、组织网络或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招揽人员从事变相传销活的。”《意见(一)》已经明确规定,对于上述 6 种非法传销行为应当根据刑法第 225 条的有关规定处理,而刑法第 225 条是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按照《意见(一)》的规定,不仅团队计酬的经营型传销行为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而且拉人头、收取入门费的诈骗型传销行为也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虽然《意见(一)》只是一个经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部门规章,并不具有刑事立法效力。但在当时我国刑事法治还不健全的背景之下,《意见(一)》对于传销活动的定罪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传销活动入罪的法律根据还是司法解释,这就是 2001 年3 月29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批复》指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粤高法[2000]101 号《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和变相传销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对于 1998 年 4 月 18 日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发布以后,仍然从事传销或者变相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实施上述犯罪,同时构成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一规定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三点:
(一)入罪的行为是从事传销或者变相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
在此,《批复》把入罪的行为表述为从事传销或者变相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从《批复》对构成要件行为的表述来看,并没有区分传销的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只要参加传销活动的,即具备了入罪的行为要件。由此可见,打击范围还是较为宽泛的。当然,《批复》还是对入罪条件做了某种限制性规定,即只有情节严重才能构成犯罪。此外,前述《意见(一)》对传销行为的表述涉及变相传销活动。也就是说,除了典型的传销活动以外,还包括变相传销活动。那么,如何界定所谓变相传销活动呢? 变相传销活动的提法来自《通知》,《通知》提出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查禁各种传销和变相传销行为。
在《通知》第三条列举的行为中,就包含了假借专卖、代理、特许加盟经营、直销、连锁、网络销售等名义进行变相传销的;采取会员卡、储蓄卡、彩票、职业培训等手段进行传销和变相传销,骗取入会费、加盟费、许可费、培训费的;以及其他传销和变相传销的行为。因此,这里的变相传销是指销售手段、入门费的称谓等形式上的不同表现。就此而言,这种所谓变相传销行为还不能与典型传销行为相提并论。
(二)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对于传销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是《批复》最为重要的内容。我国刑法第 225 条对非法经营罪的规定,采取的是空白罪状的立法方式。其中第 4 项规定的是“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是一个兜底式的规定,为《批复》的入罪解释留下了极大的余地。因此,将刑法所没有规定的传销行为解释为非法经营行为,也就成为在不经刑事立法程序而将传销行为入罪的最佳选择。
当然,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通知》本身并没有对传销或者变相传销加以界定。如果对这里的传销承袭《意见(一)》的理解,那么,在《意见(一)》规定依照《刑法》第 225 条的有关规定处理的 6 种行为中,除了第 1 种传销行为,即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组织网络从事无店铺经营活动,参加者之间上线从下线的营销业绩中提取报酬,具有经营性质以外;其他 5 种传销行为,例如,参加者通过交纳入门费或以认购商品(含服务,下同)等变相交纳入门费的方式,取得加入、介绍或发展他人加入的资格,并以此获取回报的;先参加者从发展的下线成员所交纳费用中获取收益,且收益数额由其加入的先后顺序决定的;组织者的收益主要来自参加者交纳的入门费或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的费用的;组织者利用后参加者所交付的部分费用支付先参加者的报酬维持运作的; 其他通过发展人员、组织网络或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招揽人员从事变相传销活动的。这些传销行为都没有经营内容,实际上属于以传销为名的诈骗犯罪。
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按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的还是具有经营内容的传销行为。对于诈骗性质的传销则以诈骗罪或者集资诈骗罪论处。当然,因为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因此这一界限也不明确。
因此,司法实践中存在某些定罪混乱的现象,也是在所难免的。
(三)实施传销行为,同时构成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
该司法解释在《批复》的最后,还有一句话:“实施上述犯罪,同时构成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应该说,这句话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其实,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规定。这一规定表明,在实施传销行为的时候,可能触犯其他罪名,对此应当从一重罪处断。那么,在实施传销行为的时候,会触犯什么罪名呢? 对此,在有关传销的法律规定中,其实已经有蛛丝马迹。例如,《通知》第 1 条在论及禁止传销活动的根据时,指出:“不法分子利用传销进行邪教、帮会和迷信、流氓等活动,严重背离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利用传销吸收党政机关干部、现役军人、全日制在校学生等参与经商,严重破坏正常的工作和教学秩序;利用传销进行价格欺诈、骗取钱财,推销假冒伪劣产品、走私产品,牟取暴利,偷逃税收,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对传销经营活动必须坚决予以禁止。”在此,《通知》提及传销行为可能触犯的其他罪名,包括诈骗罪、销售伪劣产品罪、走私罪、偷税罪(现已改为逃税罪)等。
传销行为在性质上的复杂性,也为此后的立法带来一定的争议。在《批复》颁布以后,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从事传销活动的行为,一般都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在少数情况下,涉及诈骗罪或者集资诈骗罪[1](P. 482) 。而两者区分的界限,就在于是否存在实际的经营活动。
案例 I 朱庆文等非法经营案 [2](P. 220 -233)
被告人朱庆文,男,1968 年 2 月 13 日出生,广西南宁市人,汉族。
2004 年 9 月底,朱庆文与王爱云以广西大顺公司、顺昌大顺公司的名义,共同策划,制定了“周周乐IC 卡”发售计划。朱庆文先后纠集、雇佣了被告人洪少彬等人参与实施该计划。该计划即以消费者直接向该公司购买螺旋藻、灵芝胶囊等保健品取得会员资格,后享受每周一次的高额返还营销款,然后以消费者所购 IC 卡金额、份额多少将会员分为业务员、业务主管、加盟商,业务主管与业务员之间存在上下线关系,上线可从其发展的下线的营销业绩中按不同比例提成,享受津贴。“周周乐 IC 卡”分为三种,即面值 360 元的健康卡、面值 1 200 元的金卡和面值 3 000 元的白金卡。高额返款即消费者每购买一份健康卡,除可提取同等价值的保健品外,每周还可获取返还的劳务费 90 元,17 周内最高返款累计 1500 元;购买一份白金卡,除可直接提取同等价值的保健品外,每周还可获取返还的劳务费 249 元,20 周内最高返款累计 4 980 元。
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朱庆文等人违反国家规定,合伙进行传销,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缴纳费用,同时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进行非法经营,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经营罪。
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25 条第(四)项、第 25 条第 1 款、第 26 条、第 27 条、第 64 条、第 67 条第 1 款、第 72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判处被告人朱庆文有期徒刑 13 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1 000 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分别判处 2 年零 6 个月至 10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一审判决以后,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审判决。
上述案例是刑法修正案(七)颁布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对传销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论处的一个典型案例。该案的“解说”(相当于裁判理由)在论及该案为什么定非法经营罪而不定诈骗罪或集资诈骗罪的依据时,指出:(1)该案传销行为存在货物买卖行为,消费者可以用“周周乐 IC 卡”刷出保健产品,朱庆文在博白龙潭有螺旋藻生产基地,向绿冬公司购买保健产品。而诈骗一般没有或者很少有货物经营行为。(2)传销的利益主要依靠传销人自己层层发展下线来获取,没有下线就没有利益。行为人陈述的周周乐 IC 卡推广计划的利润来源,主要是建立在购卡者能在消费完原面额后仍继续充值消费的基础上产生,但这种假设是不现实的。诈骗则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承诺以定期利息、红利等形式返还巨额利益相引诱。(3)报表、审计报告、账户清单和行为人供述、证人的证言可证实,行为人已经返还业务员大约几千万余元的本金及劳务费,可见确有返还大量劳务费,而诈骗返还的款项一般较小。以上对以非法经营罪论处的传销行为与诈骗性犯罪的区分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当时《通知》所规范的是指具有经营内容的传销行为。这个意义上的传销行为,是一种法律所禁止的经营行为。在上述“解说”中,就明确地把传销界定为是一种未获批准直销经营许可的行为,指出:“传销,在国外又称直销,即指用传递方式进行销售,一般是指企业不通过店铺经营等流通环节,将产品或服务直接销售、提供给消费者的一种营销方式。”在此,“解说”把传销视为是直销的营销方式,朱庆文的大顺公司所实施的传销行为之所以构成非法经营罪,是因为未获得直销经营许可。这一对传销行为的理解,把它与以传销为名所实施的各种诈骗犯罪加以区分。
然而,上述对传销的界定不仅与《意见(一)》关于传销的界定不同,而且与禁止传销条例关于传销的概念也不一致。禁止传销条例第 7 条所列举的 3 种传销行为中,所谓拉人头和收取入门费实则并无经营内容,只有团队计酬具有经营内容。当然,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拉人头、收取入门费与团队计酬竞合的情形。
二、经营型传销抑或诈骗型传销:立法过程的逆转
如前所述,在刑法修正案(七)单独设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名之前,根据司法实践的规定,对具有经营内容的传销行为(区别于以传销为名实施的诈骗犯罪)是按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的,由此而解法律根据缺乏的一时之需。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司法实践要求对传销行为专门设立罪名。我国学者指出:仅仅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传销和变相传销的性质加以规定,将传销行为纳入非法经营罪的范畴,很难适应传销和变相传销的新特点,必须独设非法传销罪,明确设定非法传销的刑罚 [3] 。对传销犯罪进行立法的建议得到立法机关的回应,并且在刑法修正案(七)中得以完成。
在刑法修正案(七)的制定过程中,对于传销犯罪如何设立罪名,存在争议,并且前后发生了重大的变更。在 2008 年8 月25 日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 稿第4 条中,对于传销犯罪是这样规定的:在刑法第225 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225 条之一:“组织、领导实施传销犯罪行为的组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犯前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传销犯罪行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这一规定是将传销犯罪的组织行为规定为犯罪,因此是一种组织罪。我国刑法中的组织行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共犯的组织行为,另一种是规定为正犯的组织行为。前者根据刑法总则的规定,以共犯论处,而并没有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后者根据刑法分则的规定,以单独犯罪论处。例如我国刑法第120 条规定的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以及第 294 条规定的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而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 1 稿对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罪的规定,就属于以单独犯罪论处的组织罪。值得注意的是,该草案还规定:“犯前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这就是说,对于具体实施传销犯罪活动的,还是按照非法经营罪、诈骗罪或者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这一规定,显然也是参照刑法第 120 条和第 294 条第 2 款的规定。如此,则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的行为构成一个组织犯罪。如果该传销组织又从事传销活动的,则根据传销的性质又分别定罪:传销而具有经营内容的,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传销而具有诈骗或者集资诈骗性质的,以诈骗罪或者集资诈骗罪论处,并实行数罪并罚。
立法机关在论及这一规定的背景时,指出:“国务院法制办、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提出,当前以‘拉人头’、收取‘入门费’等方式组织传销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危害严重。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案件主要是根据实施传销行为的不同情况,分别按照非法经营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为更有利打击组织传销的犯罪。应当在刑法中对组织、领导实施传销组织的犯罪作出专门规定。经同有关部门研究,建议在刑法中增加组织、领导实施传销行为的组织的犯罪。对实施这类犯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实行数罪并罚”。
因此,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上述规定是在原有司法解释将传销行为纳入非法经营罪规定的基础上,对组织、领导传销组织行为的特别规定。
那么,这里传销组织的传销一词如何理解呢? 换言之,这里的传销是指具有经营内容的传销还是指以传销为名的诈骗? 对此,刑法修正案(七)草案虽然并不明确,但草案有“传销犯罪行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专款规定,这里的行政法规包括前述《禁止传销条例》,而《禁止传销条例》明确把诈骗型传销和经营型传销都纳入传销的范围,因此,这是一种较为宽泛的传销概念。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上述规定,在法案审议中提出了一些意见,主要认为该罪的规定过于笼统,尤其是对传销行为按照行政法规确定,使该罪的构成要件呈现为空白状态,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为此,2008 年12 月25 日草案第2 稿第4 条中,对该罪的规定做了修改:在刑法第224 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 224 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刑法修正案(七)最后定稿也采纳了这一规定。从定稿的规定来看,不仅对传销活动进行了界定,更为重要的是将组织罪修改为诈骗性质的传销犯罪。并且,该条也从刑法第225 条之一变更为刑法第224 条之一。而刑法第224条是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从而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性质确定为诈骗犯罪。
如前所述,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 7 条对传销的列举式规定,存在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和团队计酬这三种传销方式。但在刑法修正案(七)第 4 条关于传销的概念中,只规定了拉人头和收取入门费的传销形式,恰恰没有规定具有经营内容的团队计酬的传销形式。至此,刑法修正案(七)关于传销犯罪的规定,在性质上发生了逆转:从经营型传销改变为诈骗型传销。传销这个概念在我国刑法中的界定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传销本来是一种经营方式,就此而被我国刑法确定为一种诈骗方式。
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 法教义学的考察
经过刑法修正案(七)的修正,刑法第 224 条之一规定:“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刑法修正案(七)设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以后,2013 年 11 月 14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二)》),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法律适用问题做了专门规定。对于上述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在理解与适用中存在以下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罪名的推敲
在刑法修正案(七)通过以后,2009 年 10 月 14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将刑法修正案(七)第 4 条规定的刑法第 224 条之一的罪名确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无疑,组织、领导是本罪的重要行为方式,但这一罪名概括并不全面,甚至可以说是以偏概全。因为刑法第 224 条之一的表述句式是:组织、领导……,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在这一表述中,骗取财物虽然被包裹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这一句式之中,但它却是对于本罪具有决定性的用语。在这种情况下,较为合理的罪名应该是传销诈骗罪。因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只是诈骗手段,其行为本身还是诈骗。
我们可以将刑法第 224 条之一与刑法第 224 条的规定相比,第 224 条是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规定。
在这一规定中,立法机关也列举了 5 种合同诈骗行为。但关于罪名的司法解释并没有以这 5 种行为确定罪名,而是以这 5 种行为的共同属性———合同诈骗确定罪名。如果说,5 种行为难以概括,因此不能以此为罪名。那么,我们比较刑法第194 条第2 款的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此,关于罪名的司法解释并没有根据罪状,将罪名概括为使用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罪,而是将罪名确定为金融凭证诈骗罪。因为使用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诈骗的特殊表现形态。刑法第 224 条之一也是如此,虽然条文主体内容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但基于该条文对于传销的内容界定,组织、领导这种以拉人头、收取入门费为主要特征的传销活动,其实就是一种诈骗的特殊类型。因此,以传销诈骗罪概括本罪的罪名,是最为确切的。在目前将刑法第 224 条之一的罪名确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情况下,由于在罪名中没有突出诈骗的性质,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当然,也许有人会说,传销并不必然是诈骗,因此传销诈骗一语似乎存在问题。但这里的传销诈骗是以传销为名所实施的诈骗,正如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诈骗一词,合同与诈骗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里的合同诈骗,只不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所实施的诈骗一语的简称而已。
(二)罪体的界定
根据刑法第 224 条之一的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客观上表现为组织、领导以拉人头、收取入门费为特征的传销活动,骗取财物的行为。
1.组织、领导
在刑法修正案(七)颁布之前的司法解释中,将传销犯罪的行为表述为从事传销活动。这里的从事,是指实施。因此,对传销犯罪的行为界定得极为宽泛。刑法第 224 条之一则将行为表述为组织、领导,由此表明只有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行为才构成犯罪,而一般传销活动的参与者则不构成犯罪。这一对行为的限缩,具有刑事政策的重大蕴含,体现了缩小打击面的政策思想。既然是传销诈骗罪,那么,为什么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不构成本罪呢? 对于一般的诈骗罪而言,只要参与诈骗活动的,无论是主犯还是从犯,都构成犯罪。但传销诈骗与之不同,只有这些传销诈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才是诈骗行为的实施者,而一般的参与者具有被引诱或者被胁迫的性质。虽然有些人也从传销中非法获利,但从整体上说,这些参与者还是属于被害人。正如在集资诈骗罪中,只有那些集资诈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构成犯罪,而一般的参与集资的人员,则属于被害人。
根据前引《意见(二)》的规定,下列人员可以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在传销活动中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的人员;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在传销活动中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的人员;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 1 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 15 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人员;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的人员。上述规定,虽然是以对组织者、领导者的列举式规定的形式出现的,但其中包含了对传销活动的组织、领导行为的描述。根据上述《意见(二)》的规定,传销活动中的组织行为是指传销活动中的发起、策划、操纵行为;而领导行为是指传销活动中的管理、协调行为;以及传销活动中的宣传、培训行为等。
2.传销活动
如前所述,在刑法修正案(七)设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之前,当时在法律上对于传销的理解是存在混乱的。主要问题在于:法律上的传销是指经营型的传销还是指诈骗型的传销? 显然,在对传销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的法律语境中,这里的传销只能是经营型的传销而非诈骗型的传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刑法第 224 条之一的罪状中,立法机关已经对传销做了定义式的规定。按照该规定,传销包括两种情形: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这就是所谓拉人头;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这就是所谓收取入门费。在这两种传销活动中,都没有经营的内容,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销。而是以传销为名,实际上是一种诈骗行为。
3.骗取财物
骗取财物是组织、领导传销罪的本质特征,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具有重要意义。关于骗取财物的行为,我国学者指出:“所谓骗取财物,是说由于传销行为属于非法,所以通过传销活动取得的返利、报酬等任何财产,均属于骗取财物。至于传销活动的组织、领导者实际上是否骗取到了财物,不影响本罪的构成。也就是说,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不以骗取财物为必要。所以,‘骗取财物’属于本罪可有无的概念。”[4](P. 378) 以上对于骗取财物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构成要件中的地位与意义的说法,我是不能苟同的。
首先,不是因为传销活动非法,所以通过传销活动取得的财产才属于骗取的财物。而是因为拉人头、收取入门费等方法进行传销活动,其本身就属于诈骗,因而其所取得的财物才是骗取的财物。
其次,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当然以骗取财物为其构成犯罪的要件。如果没有骗取财物的,就不能构成本罪。当然,考虑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特殊性,本罪不以骗取的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而是以发展传销人员的人数和层级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但这并不意味着骗取财物的数额对于本罪的定罪不重要。
再次,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来说,骗取财物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概念,而是不可或缺的内容。《意见(二)》对此也做了明文规定:“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采取编造、歪曲国家政策,虚构、夸大经营、投资、服务项目及盈利前景,掩饰计酬、返利真实来源或者其他欺诈手段,实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的行为,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的费用中非法获利的,应当认定为骗取财物。参与传销活动人员是否认为被骗,不影响骗取财物的认定。”而且,是否具有骗取财物的性质,也是诈骗型传销与经营型传销的根本区分之所在。
在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刑法第 224 条之一中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诈骗财物与诈骗之间的关系,存在非同一性说的见解。这种观点认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骗取财物与诈骗不是同一性质的行为。例如,我国学者指出:
刑法修正案(七)第 4 条的规定中,虽然有“骗取财物”的特征表述,但传销活动“骗取”的含义,却是推销质差、价低等,冒充高质、高价位的“道具商品”或者“服务”,通过发展下线购买的人头多少而获取相应的高额回报。也就是说,传销不是以直销产品或者实质性服务作为销售者、推介者获取利润的主要来源,而是以“拉人头”的方式,赚取“人头费”或高额“入会费”作为传销者获取利润的主要来源。但这里的传销的道具商品仍然是商品,服务仍然是服务,只是不是其所描述的商品、服务而已,这是与诈骗非同一性质的行为。[5](P. 472)
这种观点试图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骗取财物与诈骗加以区分,认为两者并非同一种行为。
笔者认为,这一理解是不妥的。以传销为手段的诈骗具有其特殊性,例如采取了拉人头、收取入门费等方法,以此骗取财物,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以此特殊性而否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骗取财物与诈骗具有同一性,这也是不可取的。
此外,张明楷教授则认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骗取财物是对诈骗型传销组织(或者活动)的描述,亦即,只有当行为人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具有“骗取财物”的性质时,才成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作为显示诈骗型传销组织(或活动)特征的“骗取财物”,不以客观上已经骗取了他人财物为前提[6](P. 748) 。这种观点肯定采取拉人头、收取入门费的手段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行为本身具有诈骗财物的性质,即承认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诈骗财物与诈骗之间存在同一性,这是正确的。但这种观点又考虑到刑法第 224 条之一所采取的“组织、领导拉人头、收取入门费,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传销活动”这一表述,认为本罪的行为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骗取财物并不是独立的行为,只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这一行为的性质。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 1 稿第 4 条将本罪的行为表述为“组织、领导实施传销犯罪行为的组织”,这是一种组织罪的立法表达。及至草案第2 稿第4 条修改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时候,仍然沿袭了先前的表述,没有相应地改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骗取财物”,而确定为“组织、领导以拉人头、收取入门费作为形式,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传销活动”的罪状。
在此,骗取财物不是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相并列的行为要素,而是用来界定传销活动的形容用语。尽管如此,笔者认为还是要把本罪的构成要件概括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骗取财物。因此,骗取财物并不仅仅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行为的性质,而且是本罪独立的客观要素。因为诈骗犯罪在构成要件上具有其特殊性,不仅要有被告人的欺骗行为,而且包含了被害人因欺骗而产生认识错误,基于这种认识错误而交付财物的行为,这才是对诈骗型传销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完整表述。
在此涉及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诈骗罪和集资诈骗罪之间的关系。对此,张明楷教授一方面认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骗取财物具有诈骗的性质;另一方面又指出:“不能认为刑法第 224 条之一与规定集资诈骗罪的第 192 条、规定普通诈骗罪的第 266 条是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进而对以传销方式实施诈骗的案件适用特别法条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论处。”[7] 张明楷教授是以如果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对诈骗型传销只能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论处,不能体现公平正义为理由,认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诈骗罪和集资诈骗罪之间不是法条竞合关系,而是想象竞合关系,以便实行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但笔者认为,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在本体上存在区分,不能因为不同犯罪的法定刑轻重设置而混淆两者之间的界限。更不赞同模糊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之间的界限的观点 [8]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作为传销诈骗罪,其与诈骗罪之间显然存在特别法与普通法的竞合关系。对此,只能按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处罚,尽管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高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至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关系,则稍显复杂。因为相对于诈骗罪而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都属于特别法。就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而言,不能认为存在特别法与普通法的法条竞合关系,但可以认为存在交互竞合关系。对此,可以按照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处理。
(三)罪责的界定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这是没有问题的。存在争议的问题在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主观违法要素如何理解。对此,我国刑法学界存在非法牟利目的说与非法占有目的说之分。非法牟利目的说认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主观违法要素是以牟利为目的。例如,我国学者指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行为人明知自己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为法律所禁止,但却通过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达到骗取钱财,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1](P. 482) 非法占有目的说则认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主观违法要素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例如我国学者指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并且具有骗取财物的目的。[9](P. 686) ”这里的骗取财物的目的完全可以理解为非法占有的目的。当然,这里没有明确地采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提法,也还是反映出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某种犹豫和踟蹰态度。
在以上两种观点中,非法牟利说是通说。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牟利目的与营利目的并无区分。
在大多数罪状中,立法者都采用了以营利为目的的表述,只有个别犯罪称以牟利为目的。无论是以营利为目的还是以牟利为目的,其前提是存在经营行为。因此,这种把以牟利为目的确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主观违法要素的观点,与对本罪的传销行为是否具有经营性的理解存在直接的关联性。在刑法修正案(七)设立本罪之前,对于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的传销犯罪,将其主观违法要素确定为以牟利为目的或者以营利为目的,都是正确的。但在刑法修正案(七)设立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传销活动是诈骗型传销的情况下,仍然承袭以牟利为目的的表述,就存在问题。笔者认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属于传销诈骗罪,是诈骗罪的特殊法。因此,对于本罪的主观违法要素,应该表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四)罪量的界定
刑法第 224 条之一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并没有规定罪量要素,但并非只要实施了这种传销诈骗行为,就一概构成犯罪。2010 年 5 月 7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二)》(以下简称《追诉标准》)第 78 条规定:“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 30 人以上且层级在 3 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根据这一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只有达到传销活动人员在 30 人以上且层级在 3 级以上的规模,才能构成本罪。
案例 II 程某等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 [10](P. 61 -63)
2012年5月底至6月初,被告人程某在博爱县打着“山东阳光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公司)”的旗号,在被告人郝某的帮助下,在博爱县清化镇重阳路以其妻子王爱利的名义设立报单中心,推销该公司无任何使用价值的电子币,以缴纳一定费用购买电子币获得加入资格,成为阳光公司的会员,并按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和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进行传销活动。
该传销活动经营模式为:每单1000元对应购买阳光公司1000电子币,每人最多购买8单,获得加入资格成为会员,每天按营销计划获得返利。会员每发展1名人员加入,可获得奖励100元。成为缴纳2000元购买2000电子币可单独设立报单中心,设立报单中心后,每向阳光公司报1单业务可获得报单费 30 元。
截至案发,程某共计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 96 人且层级达 9 级,涉案金额 481 000 元。被告人程某非法所得 14 400 元,被告人郝某非法所得 9 620 元。案发后,被告人程某退交非法所得 4 980 元。
对于本案,博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程某、郝某组织、领导以推销电子币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电子币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且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人员 96 人层级达 9 级,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程某、郝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
博爱县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41 条之一、第 67 条第 3 款、第 64 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人程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20 000 元。
二、被告人郝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20 000 元。
三、对被告人程某退交的非法所得4 980 元,予以没收。对被告人程某非法所得的9 420 元,被告人郝某非法所得的 9 620 元,予以追缴。
对于本案的定性,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程某、郝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并使他人陷入认识错误,因他人基于认识错误而自愿处分财产,行为人获取财产或者财产性利益,所以程某、郝某构成诈骗罪。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陈某、郝某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应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以上两种意见显然是按照诈骗罪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不同构成要件分别对本案事实进行了描述:诈骗罪的意见是按照行为的本质进行高度的抽象概括,形成了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使他人陷入认识错误,因他人基于认识错误而自愿处分财产,行为人获取财产或者财产性利益这样一幅诈骗罪的犯罪图景。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意见则是按照行为的表面运作进行写真式的叙述,形成了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汇总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这样一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轮廓。其实,以上两种理论叙述是对同一种行为的不同角度的表达,两者之间存在表象与本质之间的表里关系。因此,诈骗罪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客观上是竞合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如何界定诈骗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之间的关系,以便正确地对两罪加以区分呢? 对此,该案的“法官后语”指出:出现以上两种意见,其主要原因在于对骗取财物的不同理解。诈骗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区分的关键点在于主观方面:诈骗罪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行为人主观上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是具有非法牟利的动机。在传销活动中,为了不断发展人员加入,行为人通常用高额利润做诱饵,夸大或虚构佣金或奖金收入,收取高额入门费或强制购买产品,这似乎具有某些诈骗罪的特征,但传销中参加者是为追逐高额回报而加入其中,其决定交易是受到利益诱惑,而不是因虚构事实、行为误导而导致产生错误认识,故其行为不是受害人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组织者和领导者才构成本罪,一般参加者不构成犯罪 [10](P. 63) 。
对于程某等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博爱县人民法院的定性是完全正确的。但“法官后语”对诈骗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之间关系的论述则难以成立。
这里主要还是涉及对本罪的主观违法要素的理解:到底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还是与非法牟利为目的? 本案法官否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主张以牟利为目的。正如前文所言,非法占有目的和非法牟利目的的根本区分在于:客观上是否具有营利行为。如果是营利型的传销行为,主观上当然具有营利目的。反之,如果说诈骗型的传销行为,则主观上不可能具有营利目的。基于诈骗行为,主观上只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在程某等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中,已经认定被告人是以推销电子币的经营活动为名,采用传销方式,骗取他人财物。在这种情况下,主观上怎么可能具有牟利目的而不是占有目的呢?
(五)团队计酬的定性
团队计酬是传销的一种方式,被称为经营型的传销行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或者领导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传销活动的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是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
关于团队计酬到底是直销还是传销的问题,在我国法律上始终是存在模糊的。在刑法修正案(七)颁布之前,无论是在《意见(一)》还是在《禁止传销条例》中,都是将团队计酬纳入传销的范畴。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则将这种团队计酬的传销行为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但刑法理论上,也有些学者将团队计酬归入直销的范畴,认为这是直销活动中的多层次计酬。我国学者在论及拉人头和团队计酬的区分时,指出:虽然二者都采用多层次计酬的方式,但是仍有很大不同:一是从是否缴纳入门费上看,多层次计酬的销售人员在获取从业资格时没有被要求缴纳高额入门费,而拉人头传销不缴纳高额入门费,或者购买与高额入门费等价的“道具商品”是根本得不到入门资格的;二是从经营对象上看,多层次计酬是以销售产品为导向,商品定价基本合理,而且还有退货保障。而拉人头传销根本没有产品销售,或者只是以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的“道具商品”为幌子,且不许退货,主要是以发展“下线”人数为主要目的;三是从人员的收入来源上,多层次计酬主要根据从业人员的销售业绩和奖金,而拉人头传销主要取决于发展的“下线”人数多少和新入会成员的高额入门费;四是从组织存在和维系的条件看,多层次计酬直销公司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产品销售业绩和利润。而拉人头骗取传销组织则直接取决于是否有新成员以一定倍率不断加[11] 。
依笔者之见,团队计酬仍然属于传销而非直销。至于拉人头和收取入门费,则根本不是传销,而是以传销为名所实施的诈骗行为。因此,如果把团队计酬从传销中抽离,传销这个概念就不复存在了。更何况,直销是法律所允许的,而团队计酬式的传销则为法律所禁止。
在刑法修正案(七)设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并将传销界定为拉人头和收取入门费以后,团队计酬的传销形式没有包含在本罪的构成要件之中。对此,我国学者一般都认为,对于这种团队计酬的传销行为仍然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例如,张明楷教授指出:“在刑法修正案(七)公布之后,由于组织、领导原始型传销活动的行为,并不具备刑法第 224 条之一所要求的‘骗取财物’的要素,不能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又由于这种经营行为被法律所禁止,并且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依然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7] 应该说,这一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事实上,在刑法修正案(七)设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之前,司法实践中对这种经营型的传销行为本来就是按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的。在刑法修正案(七)未对这种经营型的传销行为进行规定的情况下,为惩治这种传销行为,对其按照非法经营罪论处是完全正确的。然而,2013 年 11 月 14 日《意见(二)》对团队计酬的传销行为的定性问题做了以下规定:“以销售商品为目的、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的单纯的‘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不作为犯罪处理。”与此同时还规定:“形式上采取‘团队计酬’方式,但实质上属于‘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的传销活动’,应当依照刑法第 241 条之一的规定,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处罚。”这一规定,将团队计酬的传销行为做了非犯罪化的处理。可以说,这是对传销犯罪的刑事政策的重大调整。以下将讨论的曾国坚等非法经营案,就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在司法实践中,这种刑事政策的调整对具体案件处理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当事人命运的逆转。
案例 III 曾国坚等非法经营案 [12](P. 63 -68)
被告人曾国坚,男,1974 年 10 月 17 日出生,汉族,无业。2010 年 1 月 15 日因本案被逮捕。
(其他被告人略)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曾国坚、黄水娣、罗玲晓、莫红珍犯非法经营罪,向深圳市
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09 年 6 月始,被告人曾国坚租赁深圳市罗湖区怡泰大厦 A 座 3205 房为临时经营场所,以亮碧思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发展经销商的名义发展下线,以高额回馈为诱饵,向他人推广传销产品、宣讲传销奖金制度。同时,曾国坚组织策划传销,诱骗他人加入,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入会费用,取得加入和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并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以下线的发展成员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牟取非法利益;被告人黄水娣、罗玲晓、莫红珍均在上述场所参加传销培训,并积极发展下线,代理下线或者将下线直接带到亮碧思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缴费入会,进行交易,形成传销网络:其中曾国坚发展的下线人员有郑某妮、杨某湘、王某军、杨某芳、袁某霞等人,杨某芳向曾国坚的上线曾某茹交纳人民币(以下未标明的币种均为人民币)20 000 元,袁某霞先后向曾国坚、曾某茹及曾国坚的哥哥曾某建共交纳 62 000 元;黄水娣发展罗玲晓、莫红珍和龚某玲为下线,罗玲晓、莫红珍及龚某玲分别向其购买了港币 5 000 元的产品;罗玲晓发展黄某梅为下线,黄某梅发展王某华为下线,黄某梅、王某华分别向亮碧思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交纳入会费港币 67 648 元;莫红珍发展龙某玉为下线,龙某玉发展钟某仙为下线,钟某仙发展周某花为下线,其中龙某玉向莫红珍购买了港币 5 000 元的产品,钟某仙、周某花分别向亮碧思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交纳人会费港币 67 648元。2009 年 12 月 8 日,接群众举报,公安机关联合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分局将正在罗湖区怡泰大厦 A 座 3205 房活动的曾国坚、黄水娣、罗玲晓、莫红珍等人查获。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曾国坚、黄水娣、罗玲晓、莫红珍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均构成非法经营罪,且属于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曾国坚积极实施犯罪,起主要作用,是主犯;黄水娣、罗玲晓、莫红珍均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且犯罪情节轻微,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依法均可以免除处罚。曾国坚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对其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25 条、第 25 条第 1 款、第 26 条、第 27 条、第 72 条之规定,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被告人曾国坚有期徒刑1 年零6 个月,缓刑2 年,并处罚金1 000 元;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黄水娣、罗玲晓、莫红珍免予刑事处罚。宣判后,被告人曾国坚不服,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并基于以下理由请求改判无罪:亮碧思(香港)有限公司有真实的商品经营活动,其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也没有达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立案追诉标准。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曾国坚与原审被告人黄水娣、罗玲晓、莫红珍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行为,而不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鉴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曾国坚、黄水娣、罗玲晓、莫红珍的行为已达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追诉标准,故其行为不应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论处。曾国坚的上诉理由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225 条第 1 款第(二)之规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1)深罗法刑一重字第 1 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曾国坚、黄水娣、罗玲晓、莫红珍无罪。
上述曾国坚等非法经营案,从法院认定的传销事实来看,属于团队计酬的形式。因此,公诉机关对于本案是以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的。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于本案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刑法修正案(七)施行之后,对传销活动的刑法评价应当实行单轨制,即仅以是否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特征进行评价,如果不符合该罪构成特征,就应当宣告无罪,而不能再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双轨制,认为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但并未明确取消非法经营罪的适用,对于传销活动,即使不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特征,也仍然可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在以上两种意见中,法院最终采纳了一种意见,宣告被告人无罪。在以上争论中,提及所谓单轨制和双轨制的概念。单轨制是指对于传销行为只能按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处理,这也就暗含了不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团队计酬不构成犯罪的意思。而双轨制则认为,对传销行为如果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应以该罪论处。不符合该罪特征的团队计酬传销行为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因此,这是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设立以后,对于团队计酬的传销行为究竟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所存在的争议。
显然,对于本案作出无罪判决是完全正确的。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本案提出的法律适用问题并不是“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设立以后,对于团队计酬的传销行为究竟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而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尚未达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立案追诉标准,但经营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达到非法经营罪立案追诉标准的,能否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在这一叙述中,就隐含着本案被告人曾国坚等人的传销行为,如果发展人数和层级达到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立案追诉标准,是可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论处的意思。因此,这里存在着对法律适用问题提炼上的偏差。
在本案裁判理由中,作者论述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不包括团队计酬的传销行为,团队计酬按照有关司法实践不再以犯罪论处,指出:
根据刑法修正案(七)第四条的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客观行为中未包括“团队计酬”型传销活动,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传销活动如何定性,存在一定争议。鉴于此种情况,意见(二)对“团队计酬”行为的处理进行了专门规定。《意见(二)》第五条第一款对“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的概念进行了明确。该款规定:“传销活动的组织者或者领导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传销活动的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是‘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意见(二)》第五条第二款对“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的定性进行了规定。该款规定:“以销售商品为目的、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的单纯的‘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不作为犯罪处理。形式上采取‘团队计酬’方式,但实质上属于‘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的传销活动,应当依照刑法第 224 条之一的规定,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处罚”[12](P. 67 -68) 。
显然,这段话并不是在审理本案当时的意见。因为当时对团队计酬的传销行为不以犯罪论处的司法解释还没有颁布。试想,如果当时司法解释已经颁布,对此还会存在争议吗?
与此同时,裁判理由又认定被告人曾国坚等人的团队计酬的传销行为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指出:“在本案中,曾国坚等人实施了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传销行为。客观上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特征。只是依照《追诉标准》的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立案追诉起点为‘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而现有证据显示本案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不足三十人。”[12](P. 67) 因此,本案只是没有达到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罪的追诉标准而已。如果已经达到追诉标准,是完全可以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
显然,本案裁判理由的上述两个方面的论述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案件材料反映,在一审阶段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曾建议罗湖区人民检察院就传销人员的人数和层级进行补充侦查。罗湖区人民检察院复函认为刑法修正案(七)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作了规定,但未取消非法经营罪的适用,根据刑法第 225 条第四项及《批复》的规定,曾国坚等人的行为即使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也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特征,应当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没有补充侦查必要。因此,即使是检察机关也认为,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不是是否达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追诉标准的问题,而是在刑法修正案(七)设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以后,对于团队计酬的传销行为还是否可以非法经营罪论处的问题。
之所以出现以上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情况,事实上是该案的叙述省略了时间维度有关。因为从该案材料中,我们看不到具体的审理时间。只是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的本案的案号中可以确定这是 2011年受理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的批复是 2012 年。而规定团队计酬不以犯罪论处的司法解释是2013 年 11 月 14 日颁布的。在这一司法解释颁布之前,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团队计酬的传销行为是否以非法经营罪论处,法律界限并不明确,而且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对本案以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就是十分正常的。而一审判决对被告人曾国坚等人也是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作出了有罪判决。第一次上诉以后,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发回重审。重一审判决仍然认定被告人曾国坚等人构成非法经营罪。再次上诉以后,对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逐级层报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以[2012]刑他字第 56 号批复明确:“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如未达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追诉标准,行为人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亦不宜再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据此,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被告人曾国坚等人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不足 30 人,亦没有相应证据证明该传销体系的层级在三级以上,按照疑罪从无原则,依法改判被告人曾国坚、黄水娣、罗玲晓、莫红珍无罪。
在笔者看来,曾国坚案真实地反映了在关于团队计酬的传销行为不以犯罪论处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团队计酬的传销案件如何处理问题上的一定程度的混乱。只是在司法解释正式出台以后,对于这个问题的法律界限才得以明确。但问题在于,刑法修正案(七)对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立法,本来是要加强对传销活动的惩治。但立法过程的一波三折,司法解释的限缩性规定,刑法对于传销活动的打击力度不是加强而是弱化了。
这是立法者所愿意看到的吗?不得而知。
参考文献:
[1]周道鸾、张军 主编:《刑法罪名精释》(第 4 版),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3 年版。
[2]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编:《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8 年刑事审判案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3]熊英:“对设立非法传销罪的立法思考”,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4 年第 12 期。
[4]曲新久:《刑法学》(第 2 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5]马克昌 主编:《百罪通论》(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6]张明楷:《刑法学》(第 4 版),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
[7]张明楷:“传销犯罪的基本问题”,载《政治与法律》2009 年第 9 期。
[8]张明楷:“犯罪之间的界限与竞合”,载《中国法学》2008 年第 4 期。
[9]王作富 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第 5 版),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3 年版。
[10]国家法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编:《中国法院2015 年度案例(刑法分则案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 年版。
[11]黄太云:“《刑法修正案(七)》解读”,载《人民检察》2009 年第 6 期。
[12]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编:《刑事审判参考》第 92 集,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公司决议下次,股东是否打赏的卡死了肯德基阿里
- 情感童声
- 性感男声
- 特别男声
- 普通男声
- 普通女声
- 0.7X
- 1.0X
- 1.5X
- 2X
- 3X
- 4X
- 特大
- 大
- 标准
- 小
作者
- 文章3921
- 读者2948w
- 关注1200
- 点赞1w
点睛网“点读”平台管理员账号,负责发布“点读”相关资讯,综合各类法律法规等相关文章,及时传达法律热点,便于法律人及广大群众进行学术交流和法律咨询。
【免责声明】本账号对转载、分享的内容、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善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仅供读者参考!
【版权声明】图文转载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参考之用,禁止用于商业用途。如有异议,请添加点小读微信号,告知确认后予以删除。
联系人:点小读
微信:dianjingeditor
QQ号:3244058574
邮箱:djdd@zfwx.com
思想共享 知识变现
猜你喜欢
换一换作者推荐
换一换常见问题
-
1、“点读”是什么?
点读是点睛网APP中的一款全民学法的人工智能(AI)新产品。它能“识字”和“朗读”,它使“读屏”变“听书”,解放读者的眼睛和颈椎。它使“讲课”变“写作”,解放讲师的时间和身心。
-
2、“点读”的作者?
在点睛网PC或APP端注册,登录点睛网PC端个人后台,点击“我的文章”,填写作者信息并上传文章。当第一篇文章通过编辑审核后,即成为点睛网的正式作者。
-
3、“点读”的文章?
作者在点睛网个人中心发布文章,编辑审核合格的才能呈现给读者。作者只能发布自己写的文章,不能发布或转发他人的文章。更不能发布有违法律法规、政府规定,或公序良俗、文明风尚、社会和谐等文章。
-
4、“点读”的审核?
作者文章上传后,编辑将在工作日最晚不超过24个小时、非工作日最晚不超过48个小时内完成审核。审核未通过的,说明理由。文章评论的审核,参照以上周期。



















